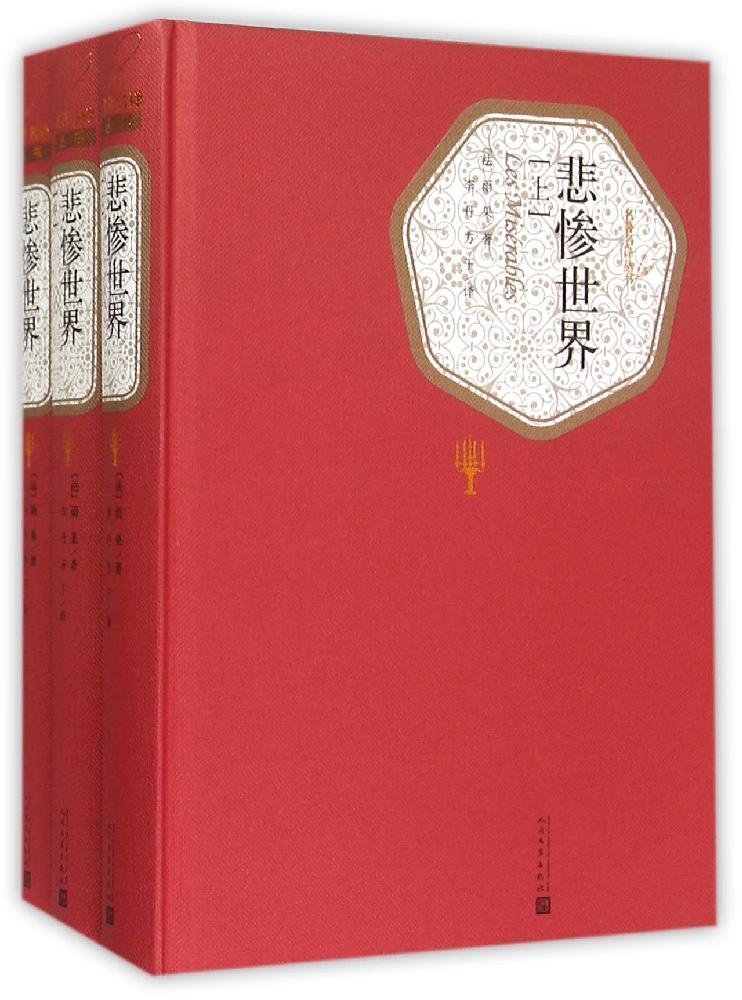
《悲惨世界》 导读
《悲惨世界》是19世纪法国的伟大作家维克多·雨果(1802-1885)的代表性作品。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,他一生跨越大半个世纪,19世纪是法国多事之秋,政治风云翻滚不息,雨果心怀天下,国内革命时曾站在广场发表演讲,支持正义者一方,为此曾流亡国外长达19年之久。普法战争爆发,在祖国危难之际,他用自己的稿费捐助了名为“惩罚”、“维克多·雨果”的大炮并回国参战。他在半个世纪里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。1885年逝世时,法国举行国哀,两百多万自愿者高举书写着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九三年》等雨果作品名字的大木牌组成了送葬队伍,,他被安葬在庄严肃穆的“伟人祠”,大殿上写着“祖国感谢伟人”。这种通常只是给予君主或军事领袖的礼遇,法国人第一次给予了一位作家。这也是文学的光荣。
《悲惨世界》是一部长达五卷的长篇巨著,也是欧洲人道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。雨果在该书序言中指出“本世纪的三个问题——贫穷使男子潦倒,饥饿使妇女堕落,黑暗使儿童羸弱”,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冉阿让、芳汀、小珂赛特的命运即分别演绎了这三个重大的社会问题。冉阿让是贯穿全书的主人公,他因为家庭贫困,不忍看到姐姐的孩子们挨饿而偷了一块面包,因此被捕入狱。期间他屡次越狱,强烈地感到社会的不公,对整个世界充满仇恨。出狱后遇到仁慈高尚的米里哀主教,在其默默无声地救助中被感动,决心以自己的余生报答米里哀的仁爱精神。他化名马德兰,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技术专利,开办了工厂并成为一名市长,造福一方土地和人民。芳汀是一名女工,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被诱奸后生下了女儿珂赛特,寄养在一家客店老板的家里。为了养活女儿,芳汀受尽恶人的盘剥,身心受辱,在生命最后奄奄一息之际,冉阿让出现,为在自己的工厂里还存有如此的不幸而自责,受芳汀之托孤,担负起了抚养珂赛特的全部责任。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和小珂赛特一样在生存线上挣扎着的儿童,寄托了作家对苦难人生的悲情关怀。后来的冉阿让在崎岖坎坷的流浪、逃难、参加街垒战等复杂经历中逐渐老去,珂赛特长大成人并获得幸福婚姻,以他们对冉阿让的衷心爱戴表达了对仁慈、博爱的回报之情。
在这部长篇中,作家描写了一个到处是苦难的世界,有社会制度的不公不义,有人性中的卑劣恶毒,有乡里习俗的恶性相向,由此而造成了男人、女人、儿童的悲惨人生。雨果在此亮起两盏明灯,一盏是宗教博爱之灯,由米里哀主教点亮,它在唤醒冉阿让的仁爱之心后,一直照耀着他的人生路途,成就了他救世救人的一生功业;一盏是革命的壮丽之灯,小说激情洋溢地描写了滑铁卢战场、街垒战斗,对那些为一种理想而战、而牺牲的英雄给予了充分的敬仰,并由一个国民代表陈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正义动机。这两盏灯的意义在于,雨果试图改造这个悲惨世界,仁爱之心拯救人性之沦落,革命之举拯救社会之危亡,两者相合,一起成就了雨果小说中那种明朗的人道主义理想。雨果曾说过:“凡是男人愚昧无知,陷于绝境的地方,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,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和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,我的《悲惨世界》都会来敲门。”
《悲惨世界》的艺术特点尤为鲜明:一是其象征性,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大都是社会各阶层的象征,尤其是冉阿让,象征着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们。二是其传奇性,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,小说中许多情节曲折离奇,给人以奇迹之感。三是其现实性,冉阿让、芳汀、珂赛特们的遭遇,无处不在控诉着现实社会中的真实苦难。四是其激情性,小说字里行间满溢情感,全书回荡着一种非凡、博大的气势。(推荐人:武跃速 人文学院教授)
阅读本书
若无法正常阅读,推荐使用江南大学"移动图书馆"

